黄友义:忆老林
编者:1月27日,中国外文局原局长、中国翻译协会顾问、“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获得者、中译外领军人物林戊荪先生,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本文作者为中国外文局原副局长兼总编辑黄友义。通过这篇记录他和林戊荪先生相处往事的文章,我们可以对林戊荪先生的国际传播思想和工作作风有更多更深入的理解。

1月27日晚上接到林局长去世的噩耗。虽然老林人已远去,但这位敬爱的领导和同事的音容笑貌犹在。
受命于困难时刻
1988年初,老林被文化部任命为中国外文局局长。那是外文局历史上最困难的一段时间。1986年,局长范敬宜调任《经济日报》总编辑,留下副局长支撑局面。1982年,外文局与文化部、对外文委、国家文物局、国家出版局等五个机构合并为新的文化部,外文局成为文化部的一个职能局,外文局下属各单位变成文化部的直属单位。文化部当时仅下属事业单位就有上百个,在那么大一个以全国文化艺术管理为主的部委里,外文局的工作肯定不是排在最前面的,一年多没有局长也就不难理解了。
听到林戊荪就任局长,许多老同事都说他是懂业务的,言谈之中表示了赞许和期待。但是,我也听到一种说法,说“老林可厉害了,他一直在《北京周报》工作,他当局长,出版社日子不会好过。”此前,我跟老林没有接触过,甚至没有机会打过一声招呼。从那以后,作为外文出版社领导之一,我经常参加他主持的会议,第一次参加他的会议,我就感到他一点儿也不厉害,就是一位纯粹的大学者。
他就任局长后,召开了一系列座谈会。有一天在会上,有几位老同事谈到历次运动中自己和他人受到的冤枉,非常悲愤,也表示了对现状的不满意。我后来猜想,一定是这些老同事了解老林,觉得终于可以把心里话倒出来了,所以发言甚为激动。老林在总结时,代表局领导对这些同事表示理解和关心,说到动情之处一度哽咽。其实,那些同事受到的不公,跟老林没有半点关系,他没有任何责任,但他却一再诚恳地道歉。
后来,外文局从文化部划出,归中央对外宣传小组代管,从业务角度看,外文局终于“找到了组织”。但那是外宣历史上一个特殊时期,国内外的形势都制约着外宣事业的发展。外文局业务跌入从未有过的低谷,事业希望渺茫,前进方向不明确,新旧矛盾合成一场危机,人心浮动,一些人纷纷调走,有一些单位都想全建制的脱离外文局,作为局长,日子有多么艰难,现在难以想象。与老林共事多年,传说中他的所谓厉害我没有见到,看到的经常是他为了单位,勤勤恳恳,苦苦支撑。从1988年到1993年初担任局长这段时间,老林遇到多少困难,受了多少委屈,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但他从来没有吐露过,更没有听他抱怨过。
国际传播的大师
如果说老林厉害,那就是他对对外宣传的娴熟,对外宣事业的满腔热情。老林从朝鲜战场回来就一直从事对外传播工作。他曾经告诉我,他在国内读完中学,先到印度学习,然后进入美国一个著名中学,继而进入一所常青藤大学,专修哲学。1991年我有幸陪同他到美国开展业务,遇到的美国人不约而同都为他的英文用词之讲究所惊叹。他一张口,对方就听出此人出身不凡,纷纷问他哪里上的学,当他说出读过的中学和大学,美国人立即表示出极大的尊重。从那以后,我深刻体会到,他是如何把自己的学问用到了我们的外宣事业。
上个世纪末期,老林从局长岗位上退下来以后,开始实践过去想做不能做的事情。他让我以中国译协秘书长的身份出面组织主要外宣外事单位的翻译,不定期研讨中译外的难点,特别是那些新出现的带有明显中国特色的时政类表述。由他坐镇,由外文出版社徐明强总编率先做东,一开始不到10个人的活动就开展起来了。外交部、新华社、经贸部、中央编译局、中国日报社和外文局的专家学者讨论并统一了一系列疑难表述的英译。
让我最难忘的是“小康社会”的英文表述。此前,社会上有多种表述,甚至有重量级人物建议就用汉语拼音。大家都知道,那样无法让对中国不理解或者知之甚少的外国人明白我们的奋斗目标。在争论之中,老林一锤定音,就是后来大家一直使用的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那天,老林引经据典耐心地给大家解释了他思考了很久的表述,说得大家心服口服,一桩在翻译界争论不休的问题终于有了大家接受的结论。


进入21世纪,各方都在创新外宣,寻求突破。时任中央外宣办主任赵启正率先垂范开展新型对外传播。他与美国一位影响力巨大的宗教界人士路易斯·帕劳进行了长达十个小时的对话。赵主任让我推荐合适的人选整理录音,编辑成书,作为对外传播的鲜活素材。把一位无神论者和一位宗教领袖站在各自立场上充满哲理的对话准确翻译成中文,我想到的第一位专家就是老林。当时,老林退而不休,在重新翻译《四书》。他意识到这次对话在对外传播上的意义,马上放下手里的活,全力投入录音整理之中。
事实证明,老林是最佳人选。他在整理中,首先发现录音里有许多翻译不准确的地方。多亏了他对西方哲学的了解和长期从事外宣的功底,纠正了口译中的错误,复原了双方讲话的真实意思,让两位观点截然不同的人既严格坚持自己的立场又心平气和的对话跃然纸上。很快,这本书由新世界出版社以中英文版出版,一时在中美两国引起轰动。两位对话人看到自己的话语,一致对老林赞叹不已,表示由衷地感谢。这本外宣的范本后来又出版了其他外文版。犹如老林一辈子的习惯,尽管老林对这本书的出版不可或缺,但在通常署名的版权页上,见不到他的名字。
原则问题不糊涂
1991年我随老林去美国,出发前,他的夫人,也是一位外宣界大名如雷贯耳的人物,国际广播电台英文部曾经的负责人张庆年老师专门给我打电话,要我在路上多关照老林,说他忘性大,经常丢三落四。我接到电话很有感慨,赞叹他们的夫妻感情,赞叹老张对老林的关心。

到了美国,我才明白为什么老张专门给我打那个电话。到美国第二天,我陪老林拜访一家发行公司,座谈的时候我和老林并排坐到桌子的一侧,我发现他手里有一个秀气灵巧的电子照相机。说实在的,那还是我平生第一次看到这种新式照相设备。会谈结束,老林把会谈材料拿上,那个相机放在他旁边的座椅上,忘得一干二净。我悄悄地拿起来,主人一边送客,一边跟老林热烈交谈,我不便为了相机打断他们,遂装入我的包里。离开的路上,老林一直跟我谈发行事宜,再也没有提起照相机的事情。
那时候,我们国家经济上很不富裕,他已经63岁了,超过1.8米的身高,坐飞机一路都是经济舱。住宿时我们两个人挤一间客房,还是快捷酒店。访问日程安排得很满,完全没有游山玩水,相机也就用不上。直到第三天,我逗老林,问他相机哪里去了,他才意识到相机不在他的手上。现在回想起来,老林顾不上照相,拿个相机也不记得使用,而我更不称职,应该拿他的相机把他跟美国人的会谈情况拍些照片。可想而知,陪他去了一趟美国,我们二人也没有留下合影。看来尽管他带了相机,拍照这件事根本不在我们的脑子里。
那次旅行快结束时,我们在一个机场候机大厅等飞机,我注意到他手里拿着一副墨镜。上了飞机后,我们的座位非常靠后。我听到一位空乘问哪位旅客把墨镜丢在大厅了。我立即按了呼叫铃。老林问我,你按铃干什么。尽管他还没有想到,我已经猜到墨镜一定是他的,果然如此。
在这些小事上老林不上心,那是因为他的注意力完全在工作和大事上。1996年,老林率领中国译协代表团到澳大利亚墨尔本参加世界翻译大会。一天,我们到我国驻墨尔本总领馆汇报工作,顺便吃饭,我听到老林非常认真跟总领事反复分析台湾的情况,全然顾不上吃喝,感到好奇。他跟我说,台湾译协想加入国际翻译家联盟,联盟之内欧美国家代表占绝对多数,因此在台湾问题上我们决不能马虎大意。那时,老林是国际译联理事,对国际翻译界的风云比我们都了解,为了维护国家立场,吃喝他早已忘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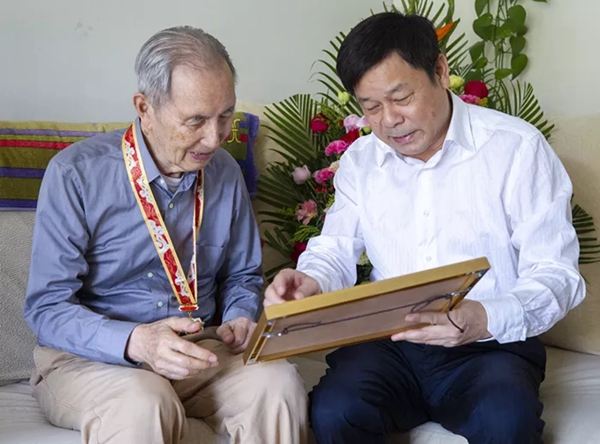
我一直把老林敬为自己的良师益友。去年下半年,听说他住院,一度病情很重,很想去看他,特别想跟他再聊翻译,回忆过去。然而,疫情防控之下,医院谢绝探望。我一直期待,等他出院后再聚。想不到已经等不到那个机会了。然而,悲痛之余,老林作为国际传播大师的学问,作为亲切的领导,作为令人特别尊重的长者,他那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他那高挺的身板,将是我永远的记忆。
作者:黄友义(中国外文局原副局长兼总编辑 )
 0
0 






c65deea4-706e-443f-b249-7abdde0ded3c.jpg)
Go to Forum >>0 Comment(s)